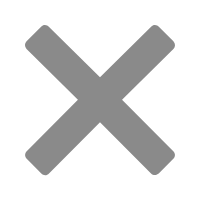-
男友说爱我时,为时已晚
第3章
那一晚,我在廉价小旅馆的床上疼到辗转反侧。
捱到天亮,几乎是爬着去拦了辆车直奔医院。
但基因崩解症,这个世界的医疗水平根本查不出根源,更别说治疗。
医生只能给我开一些止痛药来缓解症状。
我拿着药袋去办理住院手续,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,模样实在狼狈。
“哟,这不是顾助理吗?”
突然一声讥诮,我回头,看到两个前同事交换了一下眼神朝我走来。
我记得她们,是隔壁部门的两个组员,始终看我不太顺眼。
“怎么一个人来医院啊?苏总呢?没陪着你?”
“陪她?”另一个在一旁嗤笑一声,“你想什么呢?没看新闻?苏总的正主回来了,谁还管她这个冒牌货啊。”
“哈哈哈也是哦。以前靠着点见不得光的关系混进公司,人模狗样的,现在靠山没了,是不是就该滚蛋了?”
我攥紧了手里的药袋,指甲几乎要掐进掌心。
当初进公司,我拼了命地证明自己的能力,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。
可在她们眼里,永远都只是“靠男人上位”。
再加上苏宴清从不公开我,就更加坐实我“不能见光”的身份。
以前碍着他的面子,这些人只敢在背后议论。
现在,倒是毫不避讳地踩到我脸上来了。
可剧烈的疼痛让我连站直都困难,更别提开口反驳。
我只能低着头,试图从他们身边绕过去。
“怎么不说话?被我们说中了?”
两人故意挡住我的去路,语气更加恶劣:
“没了苏总,你算什么东西?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?”
“她算什么,需要向你们汇报吗?”
突然,一道冷冽的男声插了进来,我们三人同时一愣。
转过头,看见苏宴清就站在不远处,眉头紧锁,脸色不渝。
同事瞬间变了脸色,讪讪地不敢再说话。
苏宴清几步走过来,目光在那两人身上冷冷一扫:
“公司的项目是做完了?这么闲跑到医院来嚼舌根?需要我打电话给你们主管聊聊?”
“不、不用了,苏总,我们这就走,这就走……”
那两人吓得脸色发白,几乎是落荒而逃。
苏宴清的视线这才落回到我身上。
可目光里没有半分缓和,反而带着更浓的不耐烦:
“顾望舒,我昨天说得不够清楚吗?让你滚,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你现在这是什么意思?”
我想解释只是巧合,喉咙却干涩得发不出清晰的声音。
他的目光下移,瞥见我手里捏着的药袋时,眉头皱得更紧:
“拿的什么药?真生病了?”
那一瞬间,我几乎产生了一种荒谬的错觉。
他或许……还有一丝关心?
我艰难抬起手,想把手里的止痛药递过去一点,又被一道急切的声音打断:
“宴清!”
路夕夕从旁边的诊室走出来,脸色有些苍白。
一只手还捂着胸口,轻轻咳嗽了两声。
苏宴清见状,注意力瞬间被吸引过去,转身迎向她:
“夕夕!怎么样?医生怎么说?还难受吗?”
“没事,就是有点着凉,咳咳……”
路夕夕说着,又虚弱地咳了几声。
目光却越过苏宴清的肩膀,精准地落在我身上。
她的嘴角极轻微地勾了一下。
那是一个快的几乎看不见,却充满了极致嘲讽和得意的笑容。
仿佛在说,看,他关心的永远只会是我。
“都咳嗽了还说没事!快,我先送你去病房休息。”
苏宴清说完,急急忙忙带着路夕夕离开,没再过问我一句。
我又一次被彻底晾在原地,像个可笑的背景板。
尽管早就知道他会做什么选择,却每一次都忍不住怀抱希望。
说到底……是我活该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