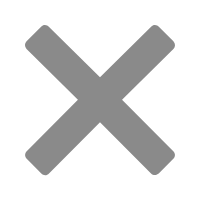-
男友说爱我时,为时已晚
第2章
苏宴清为路夕夕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接风宴。
夜晚,全城烟花齐齐绽放,几乎映红了半边天。
紧接着,无人机群升起,排列出巨大的爱心和“CC,欢迎回来”的字样。
阵仗真大啊。
为了路夕夕,他真是舍得。
我默默收回目光,看着桌上那个小小的、孤零零的生日蛋糕。
是我自己买的,插着一根“25”的数字蜡烛。
我拿起勺子,挖了一小块,送进嘴里。
真甜,甜得发腻,腻得发苦。
“宿主……”
系统的声音带着几分无力。
我咽下那口蛋糕,站起身:
“没事,习惯了。”
我不想碍苏宴清的眼,所以赶紧着手收拾行李。
所幸我的东西不多。
在这个家里,我始终像个暂住的客人,不敢留下太多痕迹。
苏宴清给我买的东西,我一件没拿,只收拾了自己带来的几件旧衣服和一些零碎。
收拾得差不多时,墙上的时钟咔哒一声,跳过了零点。
二十五岁生日,过去了。
几乎就在同时,一股难以形容的虚弱感猛地袭来。
我腿一软,直接跌坐在冰冷的地板上。
紧接着,全身骨头像被碾碎般的剧痛轰然炸开。
系统的抹杀机制开始了。
一种罕见的基因崩解症,三天,疼痛逐日递增,直到最后在极致痛苦中彻底衰竭而死。
我咬着牙试图撑起身子,但徒劳无功。
疼痛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,视线都开始模糊。
就在这时,门口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。
门开了。
路夕夕挽着苏宴清的手臂,笑着走进来。
两人看到瘫坐在地的我,都是一愣。
路夕夕微微挑眉,语气带着一丝好奇:
“宴清,这位是……”
苏宴清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毫不掩饰的厌恶和烦躁。
他皱紧眉头,声音冷得像冰:
“顾望舒?你怎么还在这里?我不是让你立刻收拾东西滚蛋吗?”
没等我开口,他立刻转向路夕夕。
脸上的冰冷瞬间融化,语气温柔得能滴出水来:
“没什么,一个……不懂事的佣人而已,我这就让她走。”
佣人?
我心里像是被冰锥狠狠刺穿,连带着身体的疼痛都麻木了一瞬。
我张了张嘴,想解释我不是故意赖着,可疼痛只能让我发出破碎的气音。
“……你怎么了?病了?”
大概是我从未有过这么落魄的时刻,苏宴清看向我时,眉眼间竟透出几分心疼。
他无意识朝我这边挪动了半步,可下一秒,又被路夕夕突然的声音打断:
“你是不是不舒服,想留在这里休息?”
“宴清你也真是的,她的状况都这么明显了,你还赶人家出去。”
只需两句话,就让苏宴清改变了想法,认为一切不过是我为了留在这里的苦肉计。
他退回原地,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:
“呵,我真是小瞧了你,竟然还跟我还演上了?装可怜给谁看?”
“以为这样我就会心软留下你?顾望舒,别太看得起自己。”
“限你三个数,自己痛快离开,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”
剧痛让我无法反驳,甚至连摇头的力气都没有,只能痛苦地喘息着。
我的沉默和狼狈似乎更激怒了苏宴清。
他彻底失去了耐心,直接拿出手机拨通了司机的电话:
“上来一趟,把客房里的垃圾和那个赖着不走的人,一起清出去。”
很快,司机上来了。
他看了我一眼:“顾小姐,得罪了。”
然后一手架起几乎无法动弹的我,另一只手拎起我那个寒酸的行李箱,几乎是拖拽着将我扔出门外。
行李箱砸在我脚边,身后的大门隔绝了里面的灯火通明和隐约传来的、苏宴清与路夕夕的欢笑声。
我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我曾经称之为“家”的地方。
然后卑微地拖着行李箱,一瘸一拐挪进了漆黑的夜色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