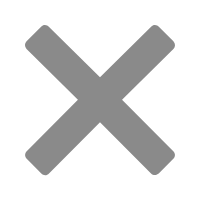-
药血
第5章
是许明朔。
许伯伯的儿子。
我来到京城后相识的人,除了萧俞,便只有他了。
许明朔比我年长三岁,我们如亲兄妹一般。
他四年前离京出走历练时,我还笑同他说:「记得早些回来,喝我和阿俞的喜酒。」
如今他回来了,脱了少年气,显出几分成熟坚毅来。
我却狼狈不堪。
「阿朔,好久不见。」
这种尴尬的情形下,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只能老套地寒暄。
许明朔张了张口,欲言又止。
他面上的表情很复杂,有心疼,有恨铁不成钢,有无可奈何。
我垂着脑袋,像做错了事。
最后他却只是端来了一碗药。
他说:「喝完,我就给你拿块饴糖。」
我苦笑:「我不是小孩子了。」
接过这碗黝黑的药汁。
上面倒映着我的脸。
憔悴而干枯。
我闭目,一口气将药汁咽尽。
放下药碗的同时,一块硬饴糖送到了我嘴边。
像小时候那样。
我下意识张口。
甜蜜在我舌尖弥漫开。
那刹那,鼻子一酸,泪水砸在碗底。
「怎么这么久不见,变爱哭了?」
许明朔无奈地笑,替我拭去眼泪。
「……阿朔。」
我哽咽。
「嗯?」
「我还能活多久?」
「……」
许明朔沉默了很久,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
「十清,你会长命百岁的。」
面对这个拙劣的玩笑话,我不知道该不该笑。
我比谁都清楚。
我活不久了。
「你不用哄我,阿朔。」
「我知道我快死了。」
许明朔腾地站起,声音微颤:「十清,你不会死的……我会找到办法救你的!」
他头也不回地出去了。
我怔怔望着他离开的方向。
嘴里的饴糖好像不甜了。
甚至有些咸的发苦。
我才反应过来。
是眼泪的味道。
这是第几次哭了?
我不记得了。
爹爹说过,我分明是个开朗爱笑的。
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呢?
是啊。
萧俞,我怎么会这样。
「爹,十清她……」
「这孩子药石无医,至多半月了。」
「……」
「明朔,你也给她诊过了,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」
「她脾脏破裂,胃疾严重,又本就气血亏虚,加上她如今愈合不了伤口,一直在失血……如今拿再多的止痛汤和参药给她,也只是吊着她一口气罢了。」
「……」
许明朔的抽泣声隐隐约约。
我早就被痛醒了,只是还在装睡。
原来我最多就只能活半个月了。
其实我感觉得到。
越来越无力。
越来越痛苦。
我以为,死亡是昏昏欲睡,是一场不醒的梦。
可死亡是一桩钟。
它悬在我头顶,每一秒都敲出振聋发聩的声响。
震颤着我的五脏六腑,一次又一次叫我温习我的痛楚。
许明朔日夜不停地照顾我。
我缓和些的时候,他想问些什么,却都没问出口。
我知道,他怕又刺激了我。
我的血止不住,便干脆叫人弄了个碗接着,拿去给许伯伯入药。
入冬了。
得寒症的人渐渐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