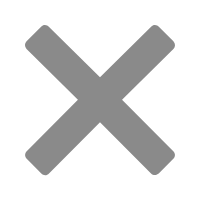-
离世第五年,妻子要我替她的竹马顶罪入狱
第3章
第二天,原本自信得意的陈矜贝显然没等到我任何消息。
我从清晨就飘在她办公室窗外,看着她第三次不耐烦地敲着手机屏幕,脸色越来越沉。
“居然真敢不理我……”
她猛地将手机反扣在桌面上,胸口起伏:
“沈赋,你长本事了是吧?!”
她以为攥着女儿的抚养费,我就一定会像以前一样低头认输,乖乖出现。
但现在,她发出的每一条威胁,都像石沉大海,再也得不到半点回响。
下午,她终于坐不住了,抓起车钥匙就冲了出去。
我跟着她的车,看着她一路开向城北——
那是我们曾经的家。
自从我跟她分开、独自带着女儿搬出来后,就再也没回来过。
她停下车,望着那栋熟悉的小别墅,眼神有些恍惚。
花园里的玫瑰早就枯死了,只剩几根顽强的杂草歪斜着立着。
秋千也锈迹斑斑,随风发出吱呀的轻响。
她站了好一会儿,才用备用钥匙开了门。
灰尘扑面而来。
客厅里的摆设还维持着原样,只是都蒙上了一层灰。
沙发上还随意搭着我以前常穿的那件灰色毛衣,餐桌上有只女儿小时候用的卡通水杯。
她慢慢走进去,手指无意识地划过积灰的桌面。
我看见她的目光停留在墙上的合影上。
照片里她笑得有点勉强,而我看着她,眼里全是光。
她很快移开视线,像是被烫到一样。
可目光所及,也全部都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切。
我没看完的书、常戴的眼镜。
墙上的贴画、我专门为她定制的茶具。
每一样,也都是我亲手布置的。
陈矜贝走到小床前,拿起一个我送她的旧旧的兔子玩偶看了很久,看到眼眶都有些发红。
然后她像是突然惊醒,猛地放下手里的,转身下楼。
她坐到客厅沙发上,再一次拨通了我的电话。
“嘟——嘟——”
电话响了很久,直到自动挂断。
她不死心,又打。
一遍,两遍,三遍。
最后,她握着发烫的手机,突然对着无人接听的电话那头低声说了起来:
“沈赋,我知道你听得见。”
“你出来吧,别躲了。”
她停顿了一下,声音压得更低,带着一种施舍般的语气:
“只要你接电话……为当年的事,跟我说句对不起。”
“说你确实拦着林野,没让他回来找我……说你错了。”
“我就原谅你。”
“我也可以不逼你顶罪了,我再找别人……只要你道个歉。“
直到最后,她的嗓音发颤,语气低低的听了很难过:
“拜托你……接电话啊。”
我飘在她面前,看着她眼里的泪光和紧抿的嘴唇,只觉得荒唐又可笑。
我根本没拦过林野。
是他自己拿了她家的钱逍遥去了,出了事才又回来找她。
我凭什么道歉?
更何况……
一个死了五年的人,要怎么接电话?
又要怎么道歉呢?
陈矜贝等不到回应,语气渐渐焦躁起来:
“沈赋!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!你……”
话没说完,电话又一次因无人接听自动挂断。
她愣愣地看着暗下去的屏幕,突然扬起手,狠狠将一旁的台灯砸在地上。
“你非要这样是吧?!好!好!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