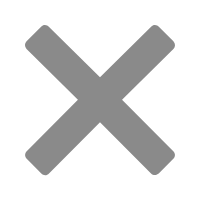-
法官妈妈为治肾衰竭的弟弟,判处了我一颗肾脏给他
第3章
四年前的那个冬天,我永远忘不了,那是我人生中最温暖又最冰冷的记忆。
那天我刚拿到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红色的封皮烫着金色的校名耀眼得让我睁不开眼。
我攥着通知书一路跑着回家,心里满是欢喜,想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爸妈妈。
可刚跑到小区门口,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,护士的声音急促又冰冷:“请问是林慧女士的家属吗?她突发急性肾衰竭,现在正在抢救,急需亲属来医院签字,并且尽快寻找匹配的肾源!”?
我手里的录取通知书“啪”地掉在地上,大脑一片空白,耳朵里嗡嗡作响,只反复回响着“肾衰竭”“急需肾源”这几个字。
我疯了一样往医院跑,冰冷的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疼,可我丝毫感觉不到。
赶到医院抢救室门口时,爸爸正焦急地来回踱步,头发凌乱,眼睛通红,看到我来他一把抓住我的手,声音颤抖:“星星,你妈她……”话没说完,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?
没过多久,医生从抢救室里走出来,摘下口罩,神情凝重地说:“患者情况暂时稳定下来了,但肾功能已经严重衰竭,必须尽快进行肾移植手术,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。你们家属尽快做配型检查吧,亲属匹配成功的概率会大一些。”
我想都没想就撸起袖子,走到护士站:“医生,抽我的血,我跟我妈配型!”
配型结果出来的那天,医生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,语重心长地跟我谈话:“林同学,你和你母亲的配型结果非常成功,这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但我必须跟你说清楚,你刚满十八岁,身体还在发育阶段,捐肾后不仅会影响你的体力和免疫力,以后还可能面临高血压、蛋白尿等并发症,而且手术本身也存在风险,你再好好考虑考虑,这不是小事。”
我透过办公室的窗户,看向病房里躺在床上、脸色苍白得像纸的妈妈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只要能救妈妈,我什么都愿意。
我毫不犹豫地在同意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,笔尖划过纸张,留下的字迹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:“医生,我想好了,我愿意捐肾,只要能救我妈,我不怕。”?
手术前一晚,妈妈在爸爸的搀扶下坐到我的病床边,她握着我的手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:“星星,是妈妈对不起你,”她的声音哽咽“让你这么小就受这种罪,妈妈这辈子都欠你的。等妈妈身体好了,一定好好补偿你,再也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”
我笑着摇了摇头,用另一只手擦去她脸上的眼泪:“妈,你别这么说,救你是我应该做的,我一点都不疼,你放心吧。”
那天晚上,我躺在床上,心里满是期待,盼着妈妈早日康复,盼着我们一家人能像以前一样好好生活,盼着妈妈说的“补偿”能早点到来。?
可手术后的日子,却渐渐偏离了我期待的轨道。妈妈身体恢复得很快,出院后却对我越来越冷淡。
以前她还会偶尔问我想吃什么,现在却连我的存在都好像视而不见。
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到39度,浑身无力,躺在床上起不来,想让妈妈陪我去医院看看她正在给林浩宇收拾书包头也不抬地挥手:“多大点事,自己找点退烧药吃就行,别小题大做。”我看着她忙碌的身影,委屈地说:“妈,我头好晕,站不起来。”她却不耐烦地皱起眉:“浩浩今天要去参加奥数比赛,我得陪他去,没时间管你。你都这么大了,这点小事自己解决不了吗?”
说完就牵着林浩宇的手,匆匆忙忙地出门了,留下我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床上。
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手术醒来后,隔壁床的阿姨跟我说的话:“你妈妈真是好福气,有你这么孝顺的女儿,愿意为她捐肾,换做别人,可不一定能做到。”
那时我还觉得很温暖,以为自己的牺牲能换来更多的母爱,可此刻只剩下刺骨的讽刺。
我从床头柜里翻出退烧药,颤抖着给自己倒了杯水吞下药片,心里的某个角落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一点点破碎。?
直到半年前,林浩宇突然被查出肾衰竭,家里的气氛彻底变了。
妈妈开始频繁地盯着我的腰看,吃饭时总往我碗里夹各种“补身体”的菜,甚至旁敲侧击地问我“最近有没有觉得腰酸背痛”“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”。
我心里隐隐不安,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底蔓延,可我还是不愿意相信,那个曾经握着我的手说要好好补偿我的妈妈,会打我仅剩一颗肾的主意。
直到法院的传票寄到家里,我看着“原告林慧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林晚星强制捐献肾脏给林浩宇”的诉讼请求,我才如遭雷击般明白,那些反常的关心,不过是为这场赤裸裸的掠夺做的铺垫。?
我发疯似的翻箱倒柜,找出四年前的手术记录、捐肾证明,还有医院开具的术后护理说明,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“捐赠者林晚星,受赠者林慧”。
我拿着这些证据去找妈妈,可她却看都不看一眼,一口咬定这些都是我伪造的:“星星,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?为了不捐肾给你弟,竟然伪造这么多假证明,你太让我失望了!”她甚至找来当初给她主刀的医生,可那个医生却支支吾吾地说:“当年的情况我记不太清了,好像确实是一位匿名志愿者捐献的肾源,可能是医院的记录出了差错。”
看着医生躲闪的眼神,我瞬间明白了,是妈妈用钱或者权力买通了他。
那一刻,我浑身冰冷,像掉进了冰窖里,终于彻底明白,我的牺牲,我的付出,从一开始就被妈妈刻意抹去了,在她心里,我从来都只是一个可以随时牺牲的工具。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