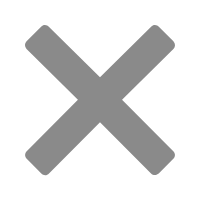-
未婚妻的竹马害我残疾,她却叫我别计较
第1章
我与沈知嫄的婚礼一拖再拖。
第一次,我的西装被浸入强酸,双腿腐蚀至今需定期植皮。
第二次,婚戒被换成放射性物质,我造血功能严重受损。
第三次,直升机螺旋桨被人动过手脚,我坠落后失去右臂。
……
所有证据都指向沈知嫄那位“患有精神分裂”的竹马周衡。
每当我崩溃质问,沈知嫄总是面露不耐:
“阿衡因我家族斗争受刺激患病,你何必与他计较?”
这次,周衡在泳池通入高压电。
我推开沈知嫄自己被电流击穿,心脏骤停三次。
沈知嫄为我输血熬红了眼。
却在出院前,我听到她打电话:
“用最贵的药,拖慢他的康复进度。”
对方震惊:“沈小姐,他为您差点没命!”
沈知嫄语气冰冷:“他欠阿衡的岂止这些?”
“阿衡受的委屈,我要他百倍偿还。”
对方沉默片刻:“那从前那些…”
沈知嫄坦然承认:“我知道的。阿衡病了,我得替他扫清障碍。”
我躺在病床,原来每道伤疤都是爱人精心设计的惩罚。
那么,如你所愿。
我正要去推门的手猛地僵在半空。
“用最贵的药,拖慢他的康复进度。”
是沈知嫄的声音,冰冷得不带一丝温度,透过虚掩的门缝清晰地传出来。
我的脚步瞬间被钉在原地,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。
“知嫄…”
另一个女声响起,语气里带着不赞同,
“苏先生刚为你挡了灾,心脏骤停三次,现在说这个不合适吧?”
沈知嫄的回应没有丝毫动摇,反而更添寒意:
“他欠阿衡的岂止这些?”
那语气里的决绝,像一把淬了冰的刀,直直捅进我的心口,
“阿衡受过的委屈,我要他一点一点,百倍偿还。”
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,几乎站不稳。
原来…原来我拼死护下的人,心里盘算的竟是如何让我更痛苦地煎熬。
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,窒息般的疼蔓延开来。
对方沉默了片刻,再开口时声音低沉了些:
“那…那从前那些意外,西装、戒指、直升机……”
沈知嫄没有任何犹豫,坦然承认,声音里甚至带着一种令我毛骨悚然的冷静:
“我知道。阿衡有精神分裂,状态不稳定,很缺乏安全感。
他只是太害怕失去了,才会做出那些冲动的事。
我得帮他扫清障碍,确保万无一失。”
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砸下。
那些我曾心疼她为此自责的意外,原来都是她默许甚至协助的“处理”?
我低头看着空荡的袖管,隔着病号服摸到腿上凹凸的皮肤,感受着胸腔里艰难跳动的心脏。这一切不是天灾,竟是我最爱之人亲手安排的结局。
对方似乎深吸了口气:“但这样对苏先生未免太…”
“好了,婉晴。”沈知嫄打断她,“我心里有数。”
“大不了等阿衡情况稳定下来了,我在补给他一个婚礼就是了。”
墙那边沉默了片刻,我听见林婉晴压低声音,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解:
“既然你这么不待见苏靖竹,何必还要勉强维持这段婚姻?离了不是更好吗。”
沈知嫄的声音突然低沉下来,带着一种压抑的烦躁:
“七年前那场连环车祸……是苏靖竹的父母刚好路过。”
她停顿了一下,声音里带着说不清的厌烦:
“他们本来可以不管的,却把卡在驾驶座的我拖了出来。
结果二次爆炸发生时,他们为了将我救出来……”
她的语气变得烦躁:
“我欠他们家一条命,要是这时候离婚,外面的人会怎么说?
说沈家忘恩负义?说我对救命恩人的儿子始乱终弃?
说我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?”
她顿了顿,声音里透出深深的厌倦:
“现在这样就很好,我嫁给他,也算还清这笔债了。
至少面子上过得去,外人也能知道我沈知嫄不是不知感恩的人。”
林婉晴似乎被这番话噎住了,沉默了几秒才开口,声音里带着明显的不认同:
“就为了不被说闲话,你要搭上人家的一辈子?
知嫄,这不是在开玩笑。”
沈知嫄叹了口气,语气依然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:
“这件事我考虑得很清楚,大不了我养着他一辈子。”
她的声音里听不出情绪,“该怎么处理我自有分寸,你不用担心。”
林婉晴似乎还想劝说:
“但苏先生他……”
“好了,”
沈知嫄温和地打断,却带着不容转圜的坚决,“这件事就到这里吧。”
我听见椅子轻微挪动的声音,应该是沈知嫄站了起来。
林婉晴也跟着起身,语气显得有些无奈:
“既然你心意已决,那我也不多说了。”
脚步声朝着门口走来,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。
门被从里面拉开,林婉晴率先走出来。
看到我时明显愣了一下,眼神复杂地张了张嘴。
最终什么也没说,只是冲我笑了笑便转身离开。
沈知嫄随后走出来,看到我时眉头立刻皱起:
“你在这里做什么?”
沈知嫄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片刻,语气平静地说:
“既然能下床走动了,那应该没什么大碍。你自己叫车回去。“
她整理了下袖口,看了眼时间:
“阿衡最近病情又反复,我得过去陪着。“
临走前她又回头补充道:
“这几天别联系我,也别在阿衡面前出现。“
她的语气依然温和,却带着不容商量的意味,
“他现在的状态受不得刺激,要是做出什么伤害自己的事就不好了。“
我站在原地,看着她转身离去的背影。
走廊的灯光照在她挺直的脊背上,那决绝的姿态比任何话语都更清晰地告诉我:
在周衡的事情上,我永远都是要被排除在外的那个。
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,我才缓缓松开一直紧握的手心,上面已经留下了几个深深的指甲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