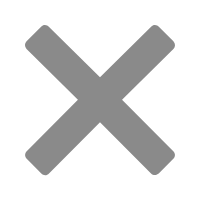-
妻子白月光闹失忆后,妻子让我签离婚协议去复合
第1章
妻子的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前任又在发脾气了。
他将我的头打得头破血流,妻子却将离婚协议递给我:“他只记得我是他女朋友,先做做样子吧,哄哄病号,等他情况好转了我们再复婚。”
我捏紧手中的婚戒,没有大吵大闹,只是沉默的点头。
干脆地签下名字。
离开前,听到她朋友的感慨:“姐夫还真听你的话,这都愿意为你做。”
“该不会后面有再过分的要求,他都不会拒绝吧。”
妻子浑身轻松的靠在椅子上:“要不要打个赌?”
她们赌一个月后的民政局,赌我会跪在地上求她回心转意,却还是听话的领完离婚证。
可一个月后,我没有哭泣,没有哀求。
离婚手续办完后,我看着手机里刚收到的消息:“我在民政局门口,你愿意出来接我吗?”
“好。”
……
父亲下葬那天,傅子明闯进灵堂,闹着让我把洛音还给她。
见我不理他。
他抄起旁边的酒瓶往我头上砸,温热的液体从我头上流下来,糊住我的眼睛。
傅子明还不解气,他环顾一周,目光直直的落在我手中的骨灰盒上。
我的心一惊,下意识的想要将手中骨灰盒往怀里藏。
傅子明却抢先一步,夺过我手中的骨灰盒,往地上砸。
啪的一声。
骨灰盒四分五裂。
看着地上的骨灰,傅子明一脚踩上去。
脸上露出一抹天真又残忍的笑容,拍手叫好:“好玩!好玩!”
我心口一滞,怨恨的情绪涌上心头,我推开傅子明,他踉跄一步,视线和我愤怒的眼神对上,他脸上的笑容瞬间一收,变成委屈。
然后坐在地上大哭大闹:“把我的音音还给我,你把我的音音藏哪里了!”
“你们都欺负我!”
我皱着眉头,想让人把他丢出去,可保安的手刚碰到傅子明,他又是一阵哭闹,尖锐的声音似乎是想将灵堂的屋顶掀翻。
就在保安的手抓住傅子明的胳膊时,洛音的声音在灵堂门口响起来。
她黑着脸,快步走过来,呵斥着保安:“松手,你有什么资格碰他。”
我看着洛音,她正小心翼翼的护着傅哲明,满脸紧张的上下安慰着他,傅哲明将脸埋在她柔软的胸口。
她却没有任何反应,而是温柔的抚摸着傅哲明的头。
这是我的妻子。
我忽然觉得我们的婚姻,在这一刻,走到了尽头。
父亲离世那天,殷切的叮嘱我,让我和洛音好好的走下去。
我注定要辜负了他的期望。
“道歉。”
洛音厉声对我说,她眼里全是厌恶。
我闭上眼,忍着心中的酸涩,指着我脸上的鲜血,指着地上的骨灰:“洛音,该道歉的人不是我,是傅哲明,他莫名其妙的闯进来……”
洛音打断我的话:“你跟一个病人计较什么?你不知道他生病了吗?如果不是你逼着我来参加你妈的葬礼,哲明也不会因为见不到我而发病了。”
她下了结论:“说到底,是你自己作的。”
我怔怔的看着洛音。
只觉得她很陌生,说出来的话让我浑身发冷。
看着地上的一片狼藉,父亲的骨灰上印着的脚印,我默默的蹲下来,颤抖着手,想要将父亲的骨灰收拢起来。
一杯水从我头顶淋下来。
是傅哲明,他笑嘻嘻的拍这手:“音音,看!落汤鸡。”
洛音宠溺的对着傅哲明笑,将我的狼狈视而不见。
她握着傅哲明的手,漫不经心的说:“阿哲心情不好,我先带他离开了,死人的地方总归有些晦气,对他身体不好。”
我张了张嘴,下意识的想挽留洛音。
至少让她送父亲最后一程。
可是看着她眼里独属傅哲明的温柔,所有的话都说不出口,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她带着傅哲明离开。
葬礼结束后,我随便找了个药店,收拾了一下头上的伤口。
回到家中,等到的不是洛音的解释,也不是洛音替傅哲明的道歉。
而是一张签了名的离婚协议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