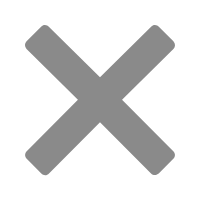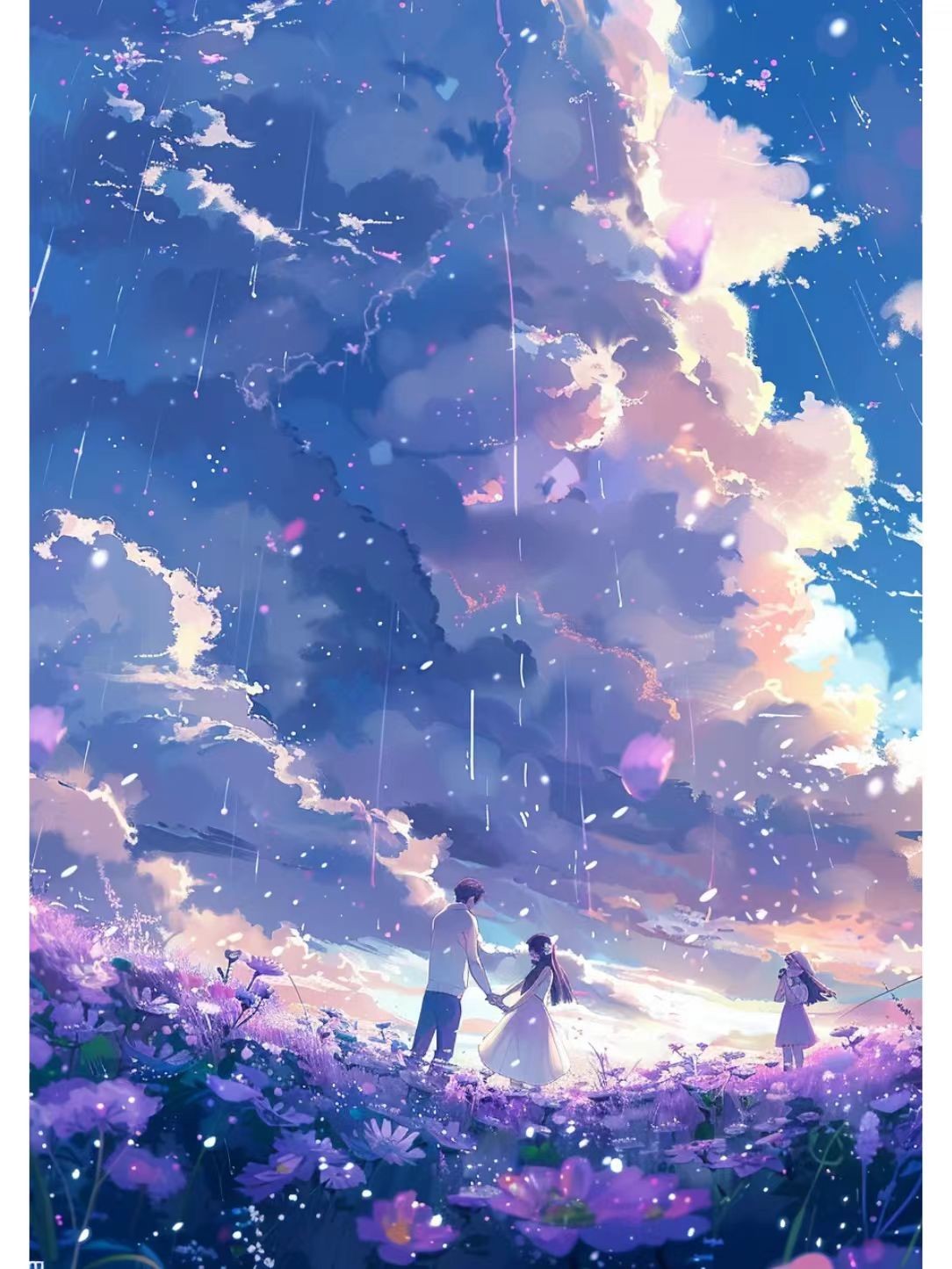
-
小叔砸锅卖铁供我上学,二十年后我出人头地回村报恩
第1章
85年,我考上北京大学后。
二叔有钱却向我哭穷,拒绝资助。
而小叔卖掉了祖传的医书供我上学。
二十年后,我回村报恩。
“我家穷得都揭不开锅了,哪有闲钱管你什么狗屁梦想!”
1985年,我带着通知书和写好的借条跪求二叔借我一部分学费。
可这个镇上唯一的“万元户”,只扔给我五十块就将我撵出了家门。
反倒是一贫如洗的小叔,竟卖掉了三本百年医书为我凑齐学费。
二十年后,我荣誉返乡,县长亲自接待我。
不想在接风宴上,我那位拜高踩低的二叔竟腆着脸跟我说……
……
午后,村口的老槐树还在蝉鸣里打盹,邮递员老王的二八自行车就“叮铃铃”地冲进了巷子。
那车铃铛,晃得比他嗓门还响:
“林耀!耀娃子!北京大学的通知书来喽!”
我正蹲在院里劈柴,闻言斧头“哐当”一声砸在木墩上。
真……真考上了?!
母亲走得早,父亲去年也没熬过冬天,这院子里就剩我一个人。
结果老王这嗓子一喊,半个村子的人跟脚后跟上了,土坯墙根下全是踮着脚张望的脑袋。
“真考上了?是北京的大学?”
隔壁李婶扒着院门往里瞅:
“耀娃你可真给咱村长脸!咱村自个儿的大学生!”
“可不是嘛!我就说这娃自小眼神亮。去年帮我算工分,小数点后两位都不带错的!”
人群中的乡亲你一言我一语,村东头的二柱子扒拉着人往前拱:
“快拆开看看!是不是跟画报上似的,红本本烫金字儿?”
老王早把牛皮纸信封塞到我手里,信封边角都被我攥得发皱。
我拆信的手的都在抖。
待“北京大学”四个烫金大字在日头下晃出光芒时,人群“嗡”地炸开了锅。
“我的天爷!北京大学!那可是全国顶顶好的学堂!”
“她爹娘要是还在,得在坟头蹦高喽!老陈家祖坟冒青烟啦!”
“以后耀娃就是吃公家饭的干部,咱村也跟着沾光!”
王大娘挤到我跟前,粗糙的手在我脑门上摸了又摸:
“好孩子,真有出息!你爹走前还念叨,说你要是考上大学,她就是砸锅卖铁也供……”
她话音没落,眼圈先红了。
我也喉头一哽没顾上接话,攥着通知书就往后山跑。
“爹!娘!”
父母的坟包前还插着去年的纸幡,我“扑通”一下跪下,额头重重磕在草皮上响了几声:
“爹,娘,我考上了!是北京大学!”
“你们对我的期望……儿子终于做到了!”
我的眼泪跟二十年来咽下去的苦水似的,又涩又烫。
可等村里人散了,煤油灯点上时,那股子热乎劲儿就凉透了。
抽屉里翻出的钱票加起来才十八块五毛,学费要两千四。
猪圈里两头半大的猪,镇上收猪的给价顶多三百。
鸡窝里那几只老母鸡,凑起来不够买半袋化肥。
这么多年能维持温饱都已经是勉强,更何况是学费……
我盯着通知书上“北京大学”四个字,指甲都快掐进纸里。
垂头丧气时,我突然想起二叔。
他是镇上第一个买彩电的“万元户”,开着杂货铺,住着红砖房。
父亲在世时,二叔总说“耀娃以后肯定有出息”。
如今我真出息了,他看在父亲的面子上,兴许也能帮衬一二?
可这借钱的事儿哪那么容易开口?
我在炕头上坐了一宿,脑袋里乱窜的念头也打架打了一宿。
直到天亮时,我犹豫再三还是写了张借条。
借条上字斟句酌,写清了还款日期,还按了红手印,连觉都来不及补就出发去了镇上二叔家。